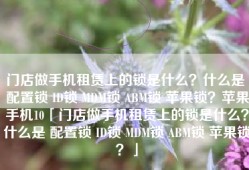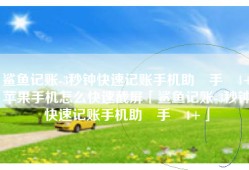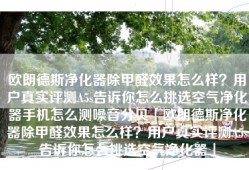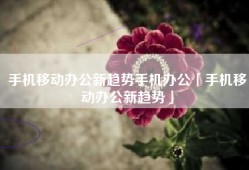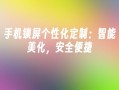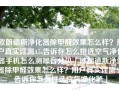贾富彬的散文 贾富彬
贾富
作者简介:贾富彬,单县孙六乡(现园艺办事处)王土城村人,1988年毕业于单县一中,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,黑龙江大学法律硕士,历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干部、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、检察日报社驻山东记者站负责人,现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、民事行政检察一处处长。办案工作之余先后出版散文集《阳台上的庄稼》、报告文学集《敬礼,中国检察官!》等。
http://s12/mw690/0060S9BTzy6YbaUXXWb2b&690 贾富彬" TITLE="贾富彬的散文 贾富彬" />
看吊孝
小时候看电影《诸葛亮吊孝》,越调名家申凤梅扮演的诸葛亮扮相飘逸,唱腔优美,特别是诸葛亮哭周瑜一段,令人荡气回肠。我看后,觉得死了人吊孝吊到这种境界真是中种享受,所以从此喜欢上了看吊孝。赶上村里谁家死了人,只要不上学,我是一定要到场的。有时因为上学或者村里老人们身体健康,没有人愿意给我提供这种欣赏机会,一两年看不到一次吊孝的,还有点失落。
谁家死了人,村里德高望重的“问事的”马上组织村里人,齐心协力帮助料理丧事。农村没有多少大事,谁家娶媳妇,可以算是村里的大事,死了人是比娶媳妇更大的事。先是召集村里的年轻人,安排分头去死者的各位亲戚家送信,叫“报丧”。接到丧讯的七大姑八大姨大多并不着急,可以当天去吊孝,也可以第二天去吊孝,只有出嫁的女儿必须马上去。女儿要哭着出自己婆家的村庄,声音尖亮,标准的女高音。一路上不哭,到了娘家村头再开始哭,一直哭到进家门和老人见最后一面。
死者躺在屋内的床板上,床板正对着屋门,门口搭起一个棚子,叫“丧棚”。亲戚来吊孝的时候,死者的子女在屋内死者旁边“守灵”,死者的本家侄子或者孙子在丧棚下面“跪棚”。亲戚来吊孝时,棚下的人和屋内的人都要陪着哭,就象陪客人喝酒一样,不能只让客人喝,主人得陪着喝。哭一阵儿,亲戚对着死者磕头,然后进屋安慰一下死者的儿女。离去时,跪棚的人要给客人磕头“谢客”。
不同的人哭法各异。如果死者是女人,其子女哭法与平时的称呼没有变化,仍叫“娘”或者“我的娘”;如果死者是男人,其子女则哭“爹”。父亲去世时,我也按照农村风俗随大溜哭了四天“爹”,不过至今我没有搞明白,好好的一个“大大”,为什么一去世就变成了“爹”。
哭时声音有高有低,有长有短,抑扬顿挫。男亲戚的哭法比较简单,平时称呼死者什么就哭“我的什么”,不是与死者感情特别深的一般不会掉眼泪,正应了那句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。女亲戚的哭则比较复杂,不仅泪如小河,显得无比悲痛,而且哭时要加进很多定语,象“我的不该走的……”、“我的受了罪的……”,能把死者的生前好处哭出大半,让人感觉死者的去世真是全体亲戚和全村人民的一大损失。
最有意思的哭,是与死者没有亲戚关系的本村邻居和邻村的村民。乡里乡亲的,礼节性地来吊孝,一批接着一批,我听过无数次仍没有听清楚哭的是什么。后向人请教,才知哭的是“我也来了——”(最后一个字拉长音)大概是对死者说:你要去天堂了,我也来了,给你送行,够哥们意思吧,以后晚上睡觉可别来吓我。还有一个原因,这么多人,特别是邻村的人,有许多是随大溜来的,搞不清和死者的辈分,也不想费力气弄清楚,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死者,有的甚至吊过孝了还不知是男是女,只好含含糊糊地一起哭“我也来了——”,自然是干打雷不下雨。
吊孝最考验人的是磕头。邻居和远亲好办,哭完后,拜一下,磕一个头就完事了。象死者的外甥、娘家侄子等要磕九个头,叫“九拜礼”——到丧棚下哭几分钟,先磕四个头,前进一步,拜一下,磕一个,站起来,后退一步,再磕四个。最隆重也是最麻烦的是死者的女婿,需要磕二十四个头,叫“二十四拜礼”——前七后八中九拜,中间还要上香、敬酒。有人不懂,为了不至于在众人面前丢丑现眼,事先在棚下练习一夜。死者的女儿也化悲痛为力量,在一旁当陪练兼技术指导。结果第二天还是记不住磕错,前排的人的碰后排的人头是常有的事。容易磕错一是二十四拜礼过程繁琐,时间长,难记;二是有很多象我这样的观众站在旁边看,看得磕头的人容易紧张;三是磕头时有乐队伴奏,听着优美动听的流行歌曲脑子容易走神。
为了显示丧事的规格隆重,一般都请人给扎纸牛、纸马楼房、电视、冰箱、手机。有的人一辈子没有见过黑白电视,死后却有了“彩电”,而且是大屏的,花花绿绿,非常好看。还要请来“响器班”来吹奏。农村乐手实在,吃了主家的饭,拿了人家的钱,吹唱起来格外卖力,专挑拿手的流行的吹,以前是《花心》、《心太软》、《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》,现在是《小苹果》。一群人围着听,高兴处拍几下巴掌。我还从没有听过吹哀乐。想想死者前几天还在被儿子打骂,死后竟迎来如此风光,真是哭笑不得。
如果死的是男人,一般停放四天;如果是女人,则停放三天。如果死者有儿女在外地工作,还没有赶回来,也可以多停放几天,等死者儿女回来见最后一面。这期间亲戚朋友该来吊孝的都来过了,出殡时只来一些关系比较近的亲戚。
出殡的前一天晚上,需要给死者“送路”——全家人扯着一块白布条幅,围着院子里的一张桌子转三圈,边转边说“某某,您走好。”然后来到村口,把桌子放下,再转三圈,对着墓地方向磕头,死者是灵魂就算认识去墓地的路了。死者生前的一些衣物也要在这个时候烧掉,烧掉了就说明送到阴间了。当年给父亲“送路”时,母亲要把父亲的拐杖烧掉,以便父亲到那边使用,不用花钱再买新的。弟媳妇说父亲到那边腿就不残疾了,用不着拐杖,不能烧。两人拿不定主意,我正悲伤着也做不出判断。把村支部书记叫来,经过几个人紧急磋商,决定让我父亲到那边不再偏瘫,拐杖不用烧了。
出殡的时间在午饭后。“喊丧的”人高喊一声“前后上肩”,意思是让把棺材抬起来。死者的儿子(儿子多的由大儿子)要将一个瓷盆摔在事先放在面前的砖上摔碎,碎片越多,后人财气越多。很多人养儿,就是等死后有人给
“摔老盆”。
十六个年轻力壮的人轮流抬棺材,棺材板很厚,加上放置棺材的“丧榆”,相当重,所以走几十米就要轮换。乡里破除迷信多年,好歹让村民接受了火化,但火化后仍要把骨灰盒放进棺材里,按出殡仪式搞一遍,足见传统概念多么根深蒂固。好不容易到了墓地,将棺材下葬,亲戚朋友再次磕头行礼,作最后的告别。死者的后代从坟头的四个角抓四把土,用穿着的孝衣包起来,回家后放在粮食缸里,预示着以后有好日子过。
喜欢看吊孝,并非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,更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,仅仅是喜欢看而已,因为看吊孝能够比看电影、看戏看出更多的东西。
我的大学